知济漫评丨在孔子的城,我们都是未写完的“子曰”
明日,曲阜的晨光会先于钟声漫过城墙。
青灰色的城砖上还沾着夜露,像岁月轻轻呵出的白雾,而整座城已屏息——不是因为即将响起的鼓乐,而是因为我们又一次站到了孔子的目光里。
这座被称作“圣城”的地方,从来不是一座凝固的博物馆,而是一片永远在生长的土壤;那些刻在竹简上的“子曰”,也从未成为句号,而是化作我们笔尖下未完成的逗点,等待续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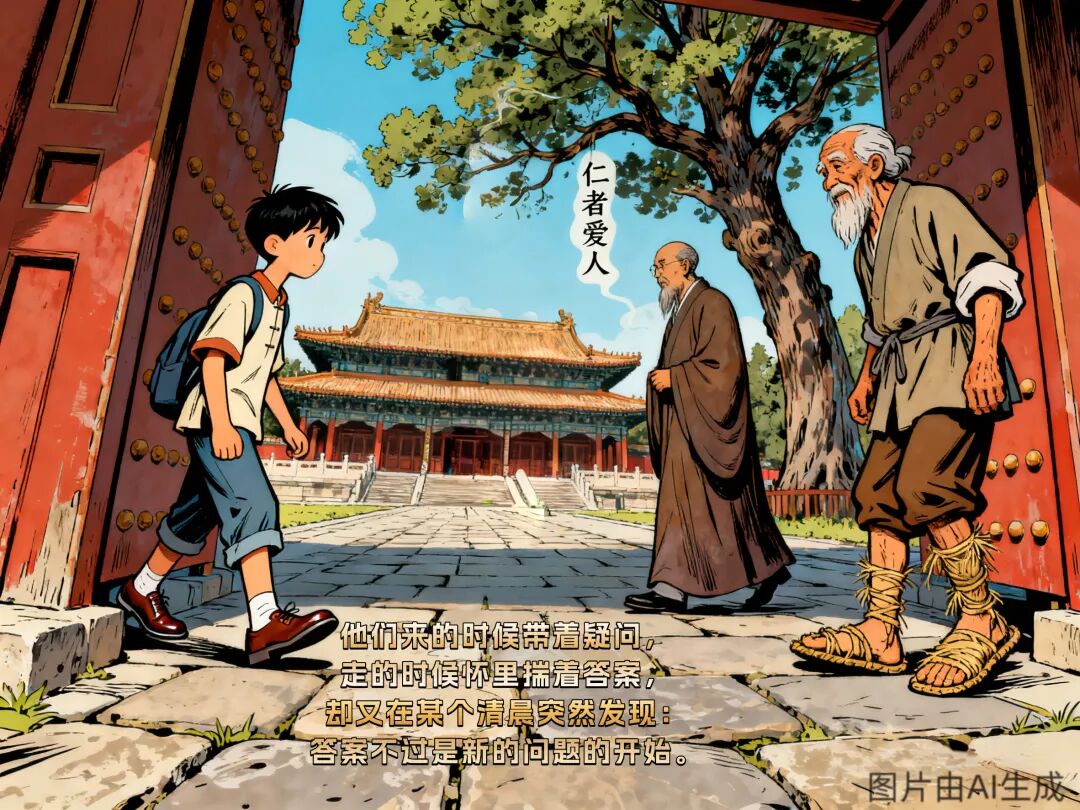
走在孔府的石板路上,脚底下的纹路里还嵌着千年的跫音。
老人们说,这宅院的门槛曾被无数双布鞋、皮鞋、草鞋踏过,从负笈求学的少年到拄杖问道的耆老,从本地童生到远道而来的异邦客。他们来的时候带着疑问,走的时候怀里揣着答案,却又在某个清晨突然发现:答案不过是新的问题的开始。
就像大成殿里那尊孔子像,始终保持着“执礼而问”的姿态——他不是在宣谕真理,而是在邀请对话;那些回荡在杏坛古树下的“学而时习之”“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”“仁者爱人”……早已浸润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,从书斋到市井,从庙堂到乡野,如同春风化雨,滋养着一代代求索者的灵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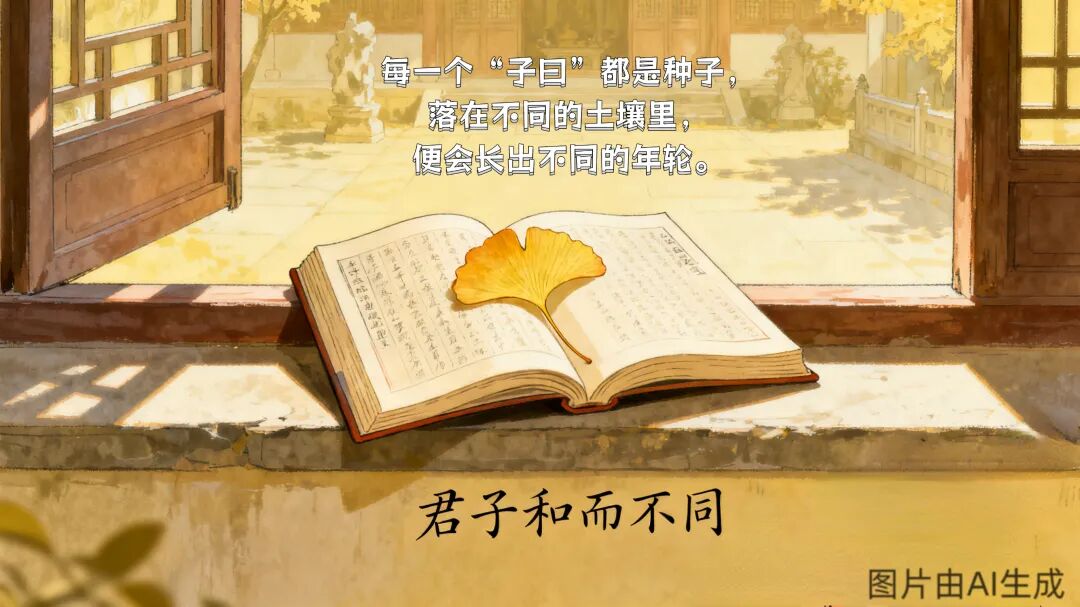
昨日经过一处静谧的庭院,见窗台上落着一本翻开的《论语》,书页间夹着一片银杏叶,叶脉里还凝着夏末的阳光。
守院人说,常有学生来这里抄录句子,有人抄“君子坦荡荡”,有人抄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有个留学生却反复描摹“君子和而不同”——他说在自己的国家,这句话像一把钥匙,解开了他与父母关于“传统与现代”的争执。
那一刻,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,墙外的喧嚣被隔绝,只剩下书页翻动的沙沙声,与千年之前的琅琅书声遥相呼应。原来,所谓“子曰”,从来不是单向的训诫,也非一成不变的终极答案,而是一个永恒开放的提问场,是无数个体生命在时代变迁中发出的回响。每一个“子曰”都是种子,落在不同的土壤里,便会长出不同的年轮。

这座城的独特之处,在于它让“古老”与“鲜活”在此相拥。
孔庙、孔府的飞檐斗拱是旧的,但掠过檐角的风声永远年轻;《论语》的竹简是旧的,但当我们在屏幕上轻触“手读论语”的互动页面,或是与孔子AI数字人对话交流,古老的智慧正以新的载体延续。
就像孔庙里千年古柏的根系,深扎于济宁这片文化沃土,新抽的枝叶正向着阳光蓬勃生长:
·尼山圣境以科技演绎儒家元素,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地标;
·孔子博物馆的数字展厅,让文物在指尖“活”起来,诉说着过去与未来;
·在鲁源村,身着汉服习“六艺”,探秘非遗工坊,与孔子AI数字人面对面,沉浸式感受儒家文化魅力;
·在教师节前夕,济宁近千所学校同步举办“敬师礼”,学子以传统礼仪致敬师长,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共振。
……
我们总以为传承是捧着旧物小心翼翼地供奉,济宁却用实践证明:真正的“两创”,是把“子曰”变成社会治理的“和为贵”品牌,变成研学课堂上的朗朗书声,变成每个济宁人待人接物的谦和与坚韧。从洙泗之滨到孔子博物馆,从尼山圣境到政德教育基地,从乡村儒学讲堂到城市文化客厅,从“新杏坛·大家讲”到蓼河夜游的灯光秀……这座城市正让传统文化从“展品”变为“活水”,滋养着发展的每一寸肌理。
9月27日,伴随着孔子文化节的帷幕拉开,整座城市都沉浸在一片庄重而热烈的儒风雅韵之中。但比这儒风雅韵,万千气象更动人的,是每个前来的人眼里的光——有白发苍苍的老教师,他的包里放着几十年来密密麻麻批注的《论语》;有背着相机的大学生,他的取景框里框住了一群诵读《论语》的孩子,记录下这份跨越时空的传承;有来自国外的留学生,正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念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……他们不是来溯源的,是来认亲的:认那个在洙泗之滨讲学的老人,认那个说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的智者,认那个把“人”字写得顶天立地的灵魂,认那个穿越两千五百年依然在问“你找到内心的‘仁’了吗”的智者。

斯文在兹,润物无声。曲阜银杏叶正染着浅黄,一片一片轻轻落在肩头,像时光写给我们的信笺。我们站在孔子的城里,手里握着的不是终点,而是续写的笔。每一个“子曰”都是未完成的诗——等着我们用今天的生活为它押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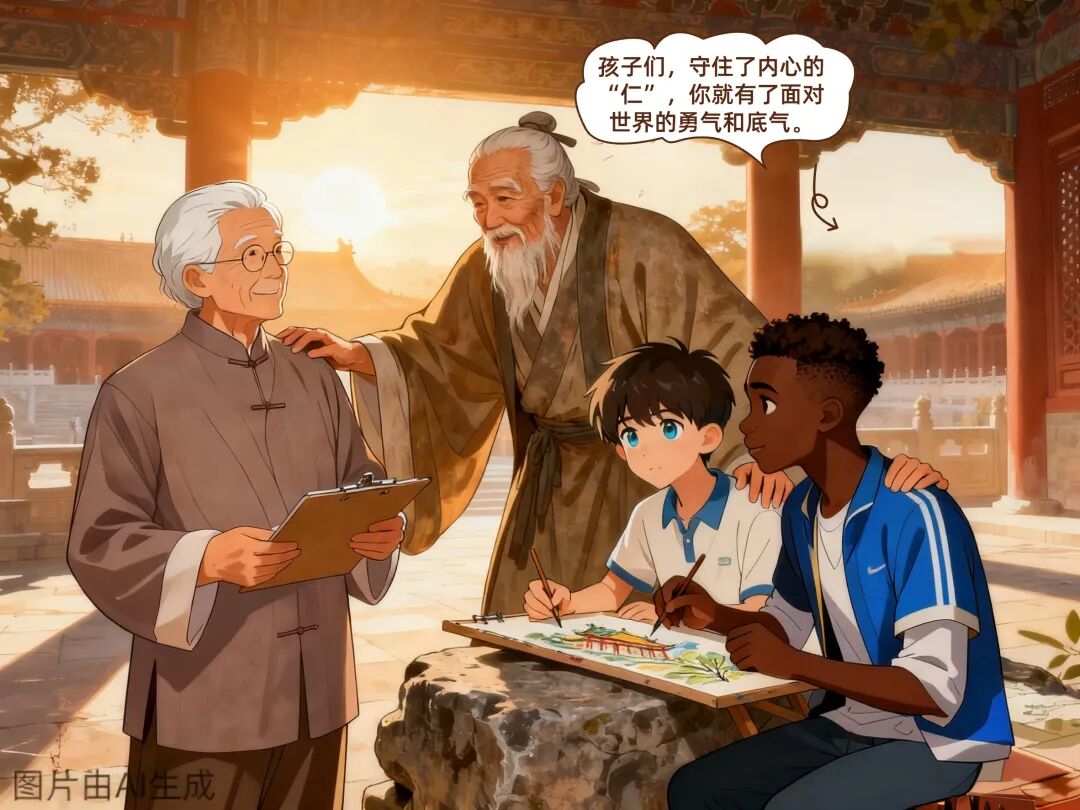
明日,当第一缕阳光再次爬上大成殿的琉璃瓦,穿越千年的鼓乐声在古城上空回荡,那声音顺着孔林的古柏根系传向四方,传进每间教室的朗读声里,传进每扇家门前的家常话里,传进每个清晨对着镜子整理衣冠的动作里……所谓传承,从来不是把古老的经典供在神龛上,而是让它活在我们的呼吸里、脚步里、每一次选择里。在孔子的城,我们都是未写完的“子曰”——而正是这份“未完成”,让文明永远年轻,让人心永远向光。
晨光里,我们仿若看见,孔子从杏坛缓缓走来,坐在我们对面,如同一位沉静而慈祥的邻家老者,拍着我们的肩膀说:“孩子,守住内心的‘仁’,你就有了面对世界的勇气和底气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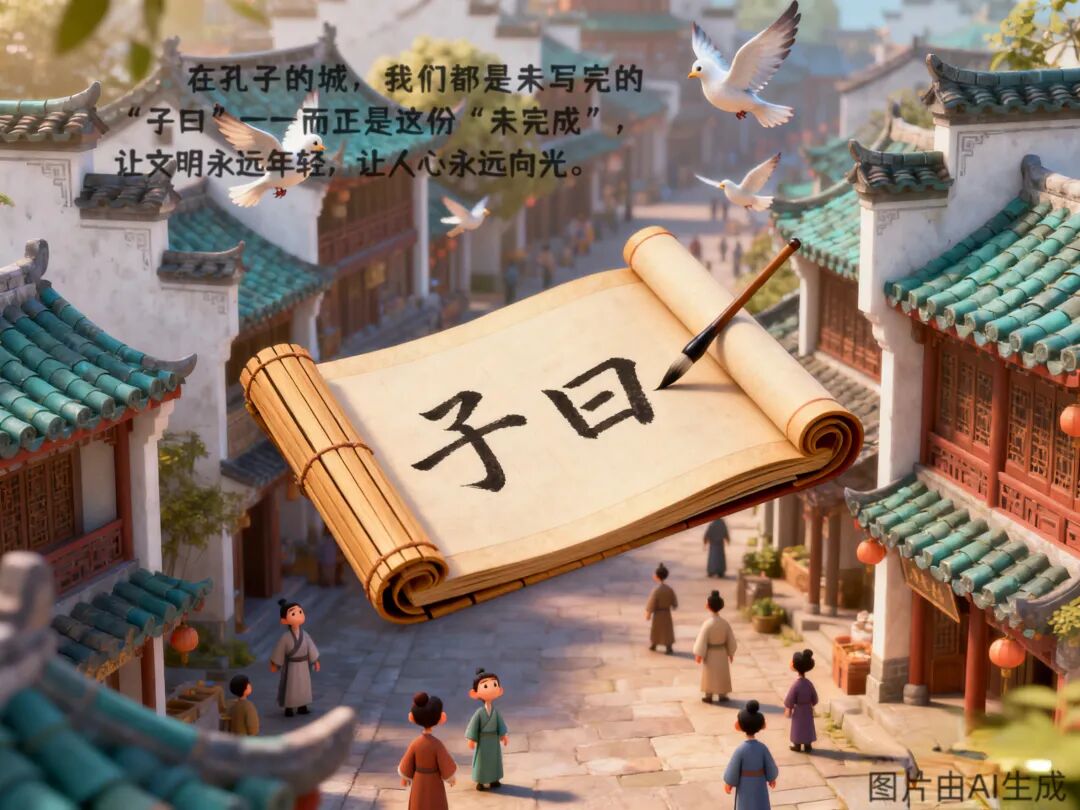


 公安备案号:37020202000242
公安备案号:3702020200024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