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勇医生被砍伤84天后出院:左手几乎没任何知觉
视频中的陶勇,穿着睡衣,左手带着复健支具坐在沙发上,头发短短的,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。4月13日,在伤害事件发生整整84天后,陶勇终于出院了。
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,陶勇一直在用右手活动着左手上的复健支具。目前他的左手还没知觉,日常生活也非常不便,全天24小时、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戴着支具,“一开始有点不太适应,但是很快就过渡过来了。”
这是陶勇出院后,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,他也首次公开袒露了受伤后的心路历程。陶勇告诉记者,他的左手很难恢复到原来那样,三个月是最佳康复期,现在主要恢复期已经过去了。
陶勇,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,从江西考入北大医学部,师从眼科权威黎晓新教授,35岁即升任副主任医师,多年来专攻葡萄膜炎的治疗。
2020年1月20日,陶勇医生在出门诊时,被诊治过的患者崔某砍伤,造成左手骨折、神经肌肉血管断裂、颅骨外伤、枕骨骨折、失血1500毫升。
在近3个月的时间中,陶勇自称“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黑暗、最沮丧的时刻” ,尽管他清醒后得知凶手身份时“很惊讶”,也想不通是为什么。
时间过去这么久,也没有等到崔某或其家人的道歉,陶勇直言,从法律层面来说,他要求严惩凶手,“不把自己埋在仇恨之中,不代表我可以宽容他、谅解他。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。”
陶勇告诉记者,如果能再次见到崔某,他会告诉其在治疗他的过程中,大家付出了很多。“我觉得我有义务让他知道,我们在给他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害他,希望他能良心发现,从医生的角度来讲,我希望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。”
受伤前的陶勇被患者称为“万里挑一的人”,因为他热情、有技术,又经常为患者着想,他和曾经的很多病人都成为了朋友,至今还有联系。
在得知他受伤后,这些病人和家属都在第一时间给他发来了微信,甚至有病人家属要将自己的手捐给他,这所有的善意都让他心怀感激,“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打击、灾难和坎坷,但是也会有很多阳光、雨露和支持,所以我很感恩。”
此次的伤害,让陶勇心有余悸,也很后怕,因为差一点就“命丧黄泉”。他说如果还能再次返回手术台,那么首先要做的是学会保护自己,这样才能更好地去帮助病人,“对于医生来说,既要有菩萨心肠,也要有金刚护法。”
伤医事件的频繁发生,让立法加快了进程。3月26日,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《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(草案)》进行一审。草案中提出,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,可以采取避险保护措施,回避对就诊人员的诊疗。在陶勇看来,安检的确可能是目前降低恶性伤医事件最可行的办法。
关于康复 重回手术台并不乐观
北青报:您身体恢复的情况如何?大家都很期望您能重回手术台。
陶勇:现在我的手在被动状态的时候还算柔软,如果拿右手去掰左手,是可以掰开的,可以说关节的僵硬程度改变了不少,一开始左手就像“鸡爪子”一样,硬邦邦的。
但是目前来说,主动的运动状态下还是不太行,左手几乎没有任何知觉。
是否能重回手术台,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。因为当时左手的神经两处被砍断,重新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。比较麻烦的是,我现在正常生活非常不方便,比如自己没办法穿衣服,没办法拧毛巾洗脸,因为这些事情靠一只手是没办法完成的。在医院的时候有护工来帮忙做这些事情,回家之后只能家人帮忙了。
北青报:您曾经说,这段时间,是您人生中最黑暗、最沮丧的时候。从医生变成了患者,您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?
陶勇: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。本身我遇到事情的时候,就喜欢往好处想,不喜欢往坏处想。之前我出诊看病人的时候,也会尽量引导病人往好的方面去想。
当然每个人在面临疾病和打击的时候,表现是不尽相同的。比如得癌症这件事情,很多人会怨天尤人,总是在想,这么小概率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,我又没做过坏事,为什么会是我呢,然后情绪上就是各种焦虑和担忧。
但也有人会乐观面对,觉得病了就病了。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新闻,两个人都得了癌症,第一个人心里没负担,觉得面对就好,情绪好,该吃吃、该喝喝,很长时间之后也没事;另一个人就不行,心情不好,整天埋怨来、埋怨去,天天吵闹,结果肿瘤没把他杀死,自己把自己吵死了。
所以说,心态很重要。我觉得在面对疾病和伤痛的时候,一定要有好心态。我当大夫这么多年,劝别人劝了无数次,轮到自己的时候,我就觉得,或许是劝人把自己的内心也劝强大了。
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,就乐观面对吧。反正手术成功了,神经肌肉血管都接上了,最终能长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吧。今后做不了手术也没关系,伤的是左手,我的右手还可以,还能拿筷子吃饭,还能够做很多事情。
北青报:在这段时间里,您心情最灰暗的是什么时候?会有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吗?
陶勇:应该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。因为那几天是最难受的,怎么呆着都不舒服,当时还有脑水肿、脑出血,头也特别疼,怎么都不舒服。加上要输很多液体,手上,胳膊上,来回扎针。
这一个星期是肉体上最痛苦的时候。痛苦到我都顾不上心里的想法。每天在病床上翻来覆去,难受,难受,就是难受,头也疼,身体也不舒服,手上还打着石膏,左手又没有知觉,哪里都难受。
无法忍受的时候倒没有,一般情况下还是忍一忍就能过去。忍不了如何,也不能咬舌自尽,人总是要能忍受得了倒霉的。不过这一个星期之后,就慢慢没那么难受了,脑水肿下去了,脑部出血也被吸收了。
关于工作 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牵挂的东西
北青报:在您清醒过来后,您曾经口述一首诗——《心中的梦》,说即使以后不能再重返手术台了,也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,让他们赚钱养家。这是否是您对于未来的规划?或者是您情绪的一种宣泄?
陶勇:在这段时间,我确实没有天天想着受伤这件事,也没有整天担心最终我能恢复成什么样,说实话,我想的更多的还是没受伤之前的事情。
原来我治好的那些失明儿童,在我受伤后,他们的家长都通过微信向我表达了关心。这些盲童,包括他们的家长,我们都交往了多年,有家长给我发微信说,要把他的手捐给我。还有一些给我转钱,但其实他们的家中条件特别差,100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,可能没什么,但对于他们来说,这是很大的一笔钱。钱我肯定不要,但我真的很感动。
我花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,我的青春全都放在了眼科事业上,但他们的举动让我觉得值得。他们把我当成家人,所以我也想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,对于这些视力不好的孩子来说,医疗技术可能已经帮不了他们什么了。我很担心孩子们,所以就写过这首《心中的梦》。
我想,如果自己的手今后不能做手术了,就做一些公益活动。比如组织这些孩子去巡演,讲一些奋发激励、与病魔勇敢做斗争的故事。用故事去卖钱,然后养活他们自己。我觉得人得病其实不可怕,怕的是失去社会属性,如果未来他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,去工作,有生活来源,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放心了。
就是说,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牵挂的一些东西。
北青报:您刚才提到的这群儿童,有没有令您印象最深刻的孩子?
陶勇:有一个跟我接触时间最长的盲童,他的本名跟香港富商一样,叫李嘉诚,后来他改名叫李天赐。他的眼睛长了恶性肿瘤,就去了我原来的单位北大人民医院治疗。
那是2003年吧,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就摘除了,那时候他才不到三岁。后来另一只眼睛也发现有恶性肿瘤,当时想尽量保住他的眼睛,制定了各种治疗方案。我们也一直在尽量给他家省钱,大家还自发给他压岁钱,给他买奶粉等。
现在过去十几年了,这名盲童的家长一直和我保持联系。他家很穷,但是知道我被砍伤的事情之后,从微信上给我转1000块钱。我知道这些钱对不少人来说,可能并不算什么。但对于这名盲童的家庭来说,可能就是两个月的生活费。
这1000块,我没有收。在我看来,很多真挚的感情,跟钱无关,它就是一种表达。我觉得在他们内心深处,可能已经把我当成他们生命中的一份子。现在这个孩子很阳光,因为当初医护人员没有因为他家贫穷而放弃治疗他,也没有歧视他,所以尽管穷,但孩子很开朗,也不自卑。
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打击、灾难和坎坷,但是也会有很多阳光、雨露和支持,所以我很感恩。
北青报:如果按照时间点来看的话,您那会应该刚成为一名医生,这件事情是否对您的从医之路有比较积极的影响?
陶勇: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只是研究生,但也从事了部分临床工作,因为我们已经有医师证了。我经常说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,因为从患者身上能学到很多人性的坚强,所以尽管这个疾病是慢性病且折磨人,但从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上,就会受到很大的鼓舞。
北青报:您曾经最高一天做86台手术,能和大家说一下那是怎样一个工作节奏吗?为什么要那么拼?
陶勇:这是七八年前,在河南南阳“健康快车”基地的时候,当年的患者都是当地比较穷困的,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做手术机会,我就想能多做一台是一台,也能让更多的人复明。对于眼科手术来说,配合的好,一天上百台手术还是能完成的。
关于受伤 现在仍后怕 但已经能正视它了
北青报:关于您受伤的事情,您现在是否能够平静的回忆这件事情?当时您正在做什么?
陶勇:很恐怖,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,因为确实差一点点,我就命丧黄泉了。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,我已经能够正视这件事了。
当天是我出门诊,正在给病人看病。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比较专心,因为来找我的都是那种病情比较复杂的疑难病人,所以每次我的注意力都会高度集中。
现在回想,我当时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有个人偷偷走到了我的身后,但我没想太多,也没在意,更不用说提高警惕性了。突然,我感觉我的头上被砸了一下,我下意识用左手去挡了一下,然后赶紧往楼下跑。之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了。
北青报: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,对吗?
陶勇:对,其实有时候医院病人多的时候,就医秩序不是很好,所以有时候你很难注意到某一个人,也很难注意到某一个人想要干什么。
北青报:您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行凶这个人是他?内心中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公平?
陶勇:过了两天才知道,那会儿的情况很混乱,我只记得他一直在我背后。知道他是凶手后,我很惊讶。也不明白为什么,因为手术没做坏,眼睛也保住了,我感慨说世事无常,如果没有尽心尽力替他保住眼睛,保住视力,他不也就没视力来杀我了吗?就觉得有点滑稽,有点荒诞。
不公平倒没觉得,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。忘恩负义的人很多,只不过他比较极端。在这一点我真没什么想不开的。
北青报:作为病人,您印象当中的崔某是什么样的人?
陶勇:他比较内向,不怎么爱说话。就是你和他说手术成功了,他也很漠然,没有任何话,没有表情,也没有什么回应。
我记得,手术之后,第二天复查完,他问“能完全恢复正常吗?”我说情况这么严重,完全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,但是能保住眼睛,也能保住一定的视力。当时他已经在我们科别的大夫那边,治疗了一年,做过两三次手术了。我们当时知道他是怀柔的农民,考虑到这个情况,别的大夫带他过来找我复查的时候,也没让他挂号,也没收费,然后打激光也没收钱。
即使如此,他见到我之后也还是没有一句话。你问我对他的印象,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没什么话的人。
北青报:您在给他做手术时,自己的身体好像也不是太好。当时是什么情况?
陶勇:三年前,我的腰受伤做过手术,当时打了钉子,后来钉子取出来了。我坐久了,其实很难受,但他眼睛的情况特别复杂,我觉得来找我的病人,大多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的,所以我轻易不会放弃。他的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,最后成功了。
北青报:崔某和他的家人后来给您道过歉吗?
陶勇:没有,他没有,他的家人也没有。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来给我道歉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,我听同事说,最初他看病的时候,还有人陪,后来也没人陪他了。其实,如果他通情达理,就会有愧疚的心,那他肯定干不出这事来。
北青报:如果再见到崔某,你会对他说什么?
陶勇:作为一名医生,如果真的有机会见到他,我会让他看一下我腰上的伤,然后告诉他,我们在救治他的过程中,付出了很多。包括我个人的努力,包括我们帮他减少费用等,至于能不能感动他,那是我无法把握的。
但我觉得我有义务让他知道,我们在给他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害他,希望他能良心发现,毕竟从医生的角度来讲,我希望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。
但从法律层面来说,我要求严惩凶手。我不把自己埋仇恨之中,不代表我可以宽容他、可以谅解他。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。
关于心态 家人的坚强和鼓励让我更加乐观包容
北青报:和您聊天时,感觉您的性格还是蛮豁达的,这和您经历的事情和成长环境有关系吗?
陶勇:我觉得这跟几点因素有关系。有一句古话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励志或者正能量的作品。例如北大学者季羡林教授,他就有本书叫《牛棚杂艺》,讲述了他自己的苦难史。我常常会想,如果我是季羡林教授,我能挺过那段日子吗?
我是从江西南城建昌镇出来的,我一直认为,如果接受信息少,很可能会变得狭隘和偏执。刚来北京的时候,我的宽容度和理解力没有现在好。但我在北京上学生活工作,又去过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,在我看来,行万里路,对提升一个人的包容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,因为在这个过程中,你会发现世界是多样性的。
当然和原生家庭的环境也有关。这次受伤,我爸为了鼓励我,讲了一件他小时候的事情。有一次,他去砍柴,不小心伤到了小腿,当时骨头都露了出来。周围没有能帮助他的人和东西,于是他自己就简单包扎一下,忍着疼,一瘸一拐地走30里路回了家。
听完之后,我就觉得跟我爸小时候比,我是不是还好点?我在医院受了伤,马上有人抢救,不像我爸,是自己一个人走30里路回的家。所以说,家人的坚强和鼓励,也是让我更加乐观、更加包容的重要原因。
北青报:受伤之后,您爸爸第一时间赶到医院,当时就提出了应该在医院设立安检。3月26号,北京市的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了《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(草案)》,里面特别提到了医院要建立安检制度,并明确了医生回避原则,对此,您怎么看?
陶勇:我觉得安检可能是目前降低恶性伤医事件最可行的办法。至于后面要怎么去改善医患关系,确实需要长期的过程。
现在有少部分患者,会利用医院息事宁人的心态,把投诉和医患纠纷当成牟利的手段。如果我们能建立社会信用评价体系,让这种想从事破坏规则并谋取利益的少部分人,在未来就业或者在他们档案上有相关记录,在他们的信用评分中也能够得到体现,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再去破坏规则。
社会环境好了,就医环境也会好。比如医院里,如果嚷嚷的声高就能插队,剩下没有一个人会好好排队,为什么?谁嚷嚷声大谁得利益。那么如果有相关评价体系,那就意味着,他出了门,就有人知道他是谁。
当然这需要长期的过程。眼下亟待解决就是,减少恶性伤医事件发生,安检的确是目前解决问题比较好的方法。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大家看到伤医是会受到严惩的,才可能会起到震慑作用,否则整个医疗秩序会更混乱。
对于医生来说,既要有菩萨心肠,也要有金刚护法。如果我还能再次返回手术台,那么我首先要做的是学会保护自己,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帮助病人。
北青报:您有过放弃医生这份职业的想法吗?或者说放弃公立医院,去私立医院工作?
陶勇:我觉得在现有医疗投入不够的情况下,医生护士的待遇普遍偏低,所以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多点执业,像我们就可以“两条腿”走路。能去私立医院为一些人服务,收入也主要在这一部分体现,在公立医院更多的就是奉献,因为不挣钱,我觉得这是合理和平衡的。
但完全放弃公立,我没想过,因为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没有标准答案,在私立医院工作,可能环境好,会比较安逸,但我觉得就失去了人生追求的高度和学医的意义。
在私立医院,给患者做手术或者看病挣钱,更多的是一份职业,而不是一份事业。但如果在公立医院能够看好疑难的、复杂的,本来都要放弃自己眼睛治疗的患者,就会特别有成就感,你会觉得你有社会价值。
北青报:医疗界有句著名的话,“有时治愈,常常帮助,总是安慰。”但是作为患者,每一次就医,都会希望自己以最快速度痊愈。那么,这句话你作为一名医生时怎么理解的,当角色发生改变时,你作为患者,又是怎么理解的?
在这个事上,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钱的问题。从本质上来说,医疗本身确实具备着不可预知性,这点我认为跟上学很像。就像老师没法保证你的孩子最好能上什么大学,因为中间的可变因素太多。
但是涉及了钱,病人就就容易把这个事看成一件商品。也因为他花了很多钱,所以就转不过这个弯。但我觉得可以让真正的良心企业、一些好的民营医院作为公立医疗的补充。
大夫可以出私家门诊,这样也能达到一个平衡。
北青报:家人对于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,如果有一天孩子问起发生您身上的这件事情,您会怎么和他说?
陶勇:家人对我还是鼓励和安慰居多。至于孩子,现在才二年级,对这些事情还没有概念,家里人只告诉他爸爸生病住院了,他也没有想太多。
如果他问我这件事情,那要看他当时的年龄,如果成年了,那就正常说。我觉得这个社会既不是性本善,也不是性本恶,善恶都在人心之中。就看你怎么去引导。对于孩子来说,我会告诉他这个世界,不是那么单纯美好,但也不是那么的邪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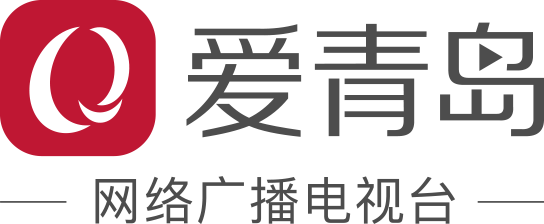

 公安备案号:37020202000242
公安备案号:3702020200024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