沧口往事:够级、沧口广场、旱冰场、大马路…
回望沧口的进行轨迹在时间的轴线上,沧口之名,明代就有了。原名为“海沧”,意思是河海交汇之处。后来,“沧口水道”的繁衍,使这里逐渐成了胶州湾的一个货运码头,沧口也是“海沧口”的简称。

《胶州志》载:“金家口、青岛口海船按装卸货物抽取税银,尽征尽解无定额;仓口、沙子、登窑三小口装花椒梨果同。”说明此时沧口的港航活动已比较正规。崂山道院和附近地区所需粮食从沧口码头上岸,通过大车和独轮车运往崂山。崂山特产也是经此装运各地。回望沧口轨迹,镌印的是一座城市的物理变迁与精神嬗变——

80年前的沧口,是青岛除市南区之外的第一大区,郊区的移民就跟下南洋似的跑到这里淘宝发展;
70年前的沧口,是青岛最大的工业区,有太阳橡胶、华新纱厂、三盛楼饭店等诸多闻名岛城的“老字号”;

60年前的沧口,是进出青岛的主要通道,沧口火车站是胶济铁路最繁忙的车站;
50年前的沧口,四流中路被叫作大马路和“沧口街”,就像中山路被叫作市里一样,是青岛仅次于中山路、辽宁路的繁华街道;
40年前的沧口,青岛仅有的两个广场之一坐落在沧口,另一个是汇泉广场。青岛所举办的任何一次群众大会,必然要在沧口广场设立唯一一个分会场;
30年前的沧口,工厂林立,是青岛人所仰慕的地方,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;
20年前的沧口,开始慢慢混同于“郊区”,不少单位招工要特别注明不收沧口户籍者。尽管那时湛山以东的大多数青岛人还是农村户口;
20年前的沧口,与李村“合并”成为李沧区,区政府东迁,留下一个城市背影;如今的沧口,青岛火车北站与海风一起自由阔大着,老工厂陆续走远,等待良久的民众等来宜居欢讯。尽管,作为一方城池的“沧口”渐行渐远,码头意义的漂泊感更是零落在风中。但在沧口曾经的生命中,那些宣泄着尘世的泥土味,却像一个城市的心事,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口口相传的历史脉络,总能带着柔软的温度,怦然心动那种。

老沧口的精髓所在
沧口的精髓所在是沧口广场,最具青岛人娱乐精神的“够级”扑克,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这里诞生并走向全国的,它所蕴涵的联邦精神甚至终结了国人以麻将为代表的个人主义。听一位老娱乐记者说,当年拍摄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,演诸葛亮的唐国强、演赵云的张山、演关羽的陆树铭等几个青岛人经常凑在一起打够级牌。他们那种如痴如醉的状态,让剧组一班人羡慕不已。据小道消息说,此后,该剧组基本上被唐国强他们演变为一个普及够级牌的短训班,摩拳擦掌的围观者被发展成够级的忠实操练者。这个不甚经典的够级故事颇具娱乐喜感,亦足以说明够级在青岛人的乐活江湖中拥有的至高无上的话语权。
延展这种历久弥新的大众娱乐精神,沧口广场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,几乎成为青岛业余生活的风向标。灯光篮球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、剧院、旱冰场、商店、饭馆、租“小人书”的书摊……鼎盛时代沧口广场拥有的这些玩具般的文化元素,以极大的濡染力,陶醉着尚单薄的大众精神生活,如同一处昂扬先驱的时代乌托邦。
沧口剧院是另外一个大众狂欢的嘉年华,白天放映电影,晚上经常有青岛话剧团、吕剧团等本地艺术团体和外地艺术团体在此上演各种剧目。一个剧院又是上映大片,又是有真人秀,这样的场景在时下也够拽的。80年代光阴的沧口故事里,不能缺席的还有沧口旱冰场。那个年代最前卫、最大胆、最漂亮的年轻人是溜冰场的标配,荷尔蒙闪闪发光的青年人,以运动系数比较高超的四轮滑冰为掩护,尽情挥霍使不完的青春,顺势拉手抑或热络,小紧张与小刺激约等于私奔。哪个年代都会发酵一批叛逆少年,溜冰场是早恋中学生的甜蜜舞台。民间传说,当时不少可爱的中学班主任会来这里“隔岸观火”,从溜冰场门口鱼贯而出的小情人们,被等在门口的老师逮个“现行”。

彰显当年时尚的“大马路”
如果说“逛市里”是青岛“土著人”曾经的摩登指向,那么“上大马路”则是老青岛另一个暖心的时尚大本营。从国棉六厂宿舍的大门往北到振华路,是沧口大马路的精华所在,曾集中了几代沧口人的快乐生活向往,留驻了无数人的“一路春风”。在这段500多米的路上,七七八八地布满了药店、鞋店、书店、布店、奶站、医院、学校、邮局、百货店、服装店、家电店、文具店、食品店、理发店、五金店、照相馆、电影院等最完备的生活要素。对待那个年代酝酿的潮流,亦能以星火燎原之势敏锐而迅捷地乘胜追击。
路北头那家“三盛楼”饭店是老青岛的“四大楼”之一,亦曾是青岛市名噪一时的“大酒店”。20年前,大家流行在家里搭棚子结婚请客的时候,谁要能在“三盛楼”摆上标准为30元一桌的酒席,级别相当于现在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婚宴。即使是彼时最华丽的美食地位,最好的菜肴也不过是青椒炒瘦肉片和炸虾。
国棉厂里飞扬的青春

沧口,飘散在心头的怅然若失,还有国棉厂。在过去很多年里,青岛常与一个“上青天”的词儿联系在一起。那时,青岛与上海、天津一道扛起全国纺织业的大旗。国棉厂是那个时代如日中天的发光体,所有的光华定格在一个春光最盛的时代。往事并不如烟,尽管国棉厂随着光阴流转渐行渐远渐淡然,但时光的背影,流转到如今依然温存。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的40年里,曾经走过最飞扬的历程。那时候,10个国棉厂从老四方绵延到北部的娄山后,蔚为壮观。其他以纺、织、染为业的厂家更是星罗棋布。国棉厂的厂区多是和宿舍连在一起,内部系统如同一个高效运转的大机器,精细而周全。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小学、俱乐部、澡堂、食堂、商店、粮店、医院、产院、电影院、图书馆、招待所,一应俱全。甚至,一些国棉厂还有自己的铁路线,直接与胶济线通联。国棉厂自给自足,绝对是不折不扣的卫星城。

国棉厂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。如同那个时代所氤氲的灿烂、青春的特质,国棉厂暗合的素朴光芒,在过去许多年后,依旧闪烁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适龄的青年,成为一名国棉厂工人,就跟现在当公务员一样火热。漂亮、泼辣、能干、隐忍的纺织厂女工像诗里熠熠生辉的美丽章节,也几十年如一日地领导着城市的时尚潮流。能找个纺织女工当老婆,绝对是那个时代男青年的最高追求。对了,有一个轰动一时的歌舞叫作《金梭和银梭》,就是歌颂纺织女工的。


艺术是唯美的,工作却是现实的。在一年四季高湿的车间里,在织机巨大声浪的轰鸣中,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,一个班独立穿梭在二三十台织机中接线头,走二十多公里的路极其平常。这还并不是最枯燥的,她们常年三班倒,生物钟完全紊乱,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。对她们而言,能舒服安逸地睡上一觉,无疑是最朴素的幸福。
那时,如果能有幸被选入“郝建秀小组”工作,无疑是纺织女工最崇高的理想。而如果能找一个毗邻厂区的军校或军营的英俊军官做恋人,便是很圆满的生活状态了。那时参加工作多流行顶替,当纺织工人几乎成为一种尊贵的世袭制,纺织工人家庭的孩子似乎是天底下最无忧甜蜜的孩子。

以时间代入者身份建立了“沧口式”城市生活样本的不仅有国棉厂,还有“生活在别处”的城中村。营子村、板桥坊村就像一颗蓬勃的种子,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粗粝地生长,强悍地把沧口记忆塞得满满的。尽管,这里已然滑出时代大背景的轨道,更多行使的是一种穿针引线、相濡以沫的时空功能。但沧口如同城市的夜游症,总能在万籁俱寂中与往事深呼吸,让缭乱的心安然舒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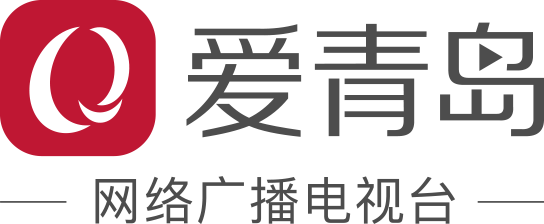

 公安备案号:37020202000242
公安备案号:3702020200024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