磨难与成长|记录两个骨肿瘤儿童的家庭
15岁的思思躺在床上,望着窗外的目光似乎毫无焦点。高高低低的楼顶填满窗框的长方形构图,一个多月里天天如此。唯有颜色丰富些,不像病房只有白色、乳白色、米白色。
隔壁床的人在闭目养神。最外侧靠墙的老太太用方言和老伴絮叨着,忽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。思思皱起眉,翻出手机来捣鼓,忽然冒出一句:“我想回家。”
她说自己烦死了,又朝着老太太的方向撇撇嘴,小声嘟囔:“整天(喊着)要死要死的。”
思思妈在一旁正发愁:女儿的靶向药到底吃不吃呢?吃,价格昂贵,且副作用严重。可如果不吃,听医生的意思,女儿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。

思思在病床上看手机。这是她唯一可以用于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。澎湃新闻记者章文立图
辗转求医路
思思家住江苏省如皋市下的一个村庄,父母十几年前就出门打工,在苏州开一家做羊毛衫整烫的小工厂,一年回家一两次。
2017年6月底,思思的老师打电话说孩子住校总喊腿疼。夏季生意少,思思妈正好在家,便带她去看村里的赤脚医生。医生没摸出什么来,只嘱咐去买膏药敷一敷。
敷了几天,腿更疼了。适逢期末,思思不想耽误复习,硬是撑到考试结束。去镇上的医院拍X光片,医生说青春期的孩子发育快,可能在长骨头,建议回家熬点骨头汤,买钙片吃。
思思妈当晚就买了大棒骨煲汤。半夜思思还是疼醒,妈妈起来帮她揉腿,稍稍用力,她就痛得尖叫起来。碰巧几日后应朋友之邀去如皋市区,思思妈想:“顺道带她去县医院看看吧。”
6月30日,思思在如皋市第一人民医院拍了CT。第二天早上,母女俩逛街买衣服正高兴,医院打来电话。思思妈一下子坐在路边,半天没爬起来——检查结果“不太好”,医生建议转院。
同村小伙介绍了一位南京的医生,人在上海。思思爸当即开车从苏州回如皋接人,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。医生看完片子,建议再做个肿瘤病理切片检查。一家人又连夜赶回如皋。7月3日,思思做了穿刺活检。这次,南京的医生只给了一个建议: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。
两天后,思思出院并赶往上海。在车上她已是半躺状态——自穿刺活检后,她的左腿就很难行动了。7月6日早晨,思思入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,检查后被确诊为骨肉瘤。
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骨肿瘤,多发生于10岁至20岁的青少年,发病率大约为百万分之一至三。由于罕见,很多基层医生终生都碰不到一次,认识不足,也没有治疗经验。患者年龄小、正值青春期等情况,又常使初期症状被忽视。在思思自己的回忆中,她4月时就抱怨过腿疼,而思思妈对此毫无印象。
但相比于无人指点而盲目辗转于各个医院的患者,思思已算幸运。她入院时,10岁的小胖已受了半年折磨。
小胖1月就觉得胳膊疼,可他怕痛、怕打针,拍过一次X光片后就不愿进一步检查。平时又喜欢体育运动,常有磕碰,家人就没太在意,只买了膏药给他敷。
2017年春节后,妈妈看小胖脸色和胃口都急剧变差,才终于带他又去了一次医院。他做完核磁共振,医生觉得80%的可能是肿瘤,建议转院。
转院要重新排队,又一轮检查、穿刺活检,最终确诊时已是3月底。肿瘤科床位紧张,小胖又等了十几天才入院。此时据他最开始喊“胳膊疼”,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。
做了一个疗程化疗后,肿瘤仍在生长,几乎不见效果。出院时,医生委婉地建议小胖妈:“休养这段时间,你们可以去走走看,有没有别的好医院。”小胖妈懵了: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,在当地人的意识中已经是最好的医院了,再找,往哪儿找?
她四处求人、打听,最终在朋友的建议下,去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,预约挂号肿瘤科。肿瘤科医生解释了科室区别,建议去约骨科专家;重新预约到骨科,门诊医生又对症推荐了一位骨肿瘤专家;然而专家号已经排到两周后,不知道能不能约上。
小胖妈几乎是绝望的,她求人家:“万一真的排不上怎么办?你们在上海比较清楚情况,能不能再给一些其他医院推荐?”至此,她终于第一次听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肿瘤专科。那时小胖的胳膊已肿到两三倍粗,肿瘤压迫上臂骨折。
上海求医期间,考虑到宾馆贵,小胖妈决定找个私立医院先住着,也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私立医院给出的方案是“血管介入法”,即利用导管插入动脉或静脉,通过堵住营养肿瘤血管血流来阻止肿瘤继续增大,促使肿瘤组织坏死。但医生看他情况严重,没敢直接治疗,建议继续找专家咨询。
2017年5月8日,飞抵上海的第12天,小胖妈终于约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,正好碰到上海市骨肿瘤研究所所长、骨科主任蔡郑东值班。“他说怎么(发展到肿瘤)那么大才来。我说在我们那边(耽误)那么久了,来上海人生地不熟,又约不上医院……他就说,马上住院,不能再拖了。”小胖妈回忆。
当天下午小胖就办了入院手续。但检查结果显示,肿瘤已经发生了肺转移。蔡郑东很惋惜:“骨肿瘤本身不致死,但转移性很强。一般来讲,肺转移的小孩会在一年左右走掉。”
据他介绍,国外(如日本)有严格的转诊制度,一经发现就会转到比较著名的专科诊疗中心,因此生存率较高。国内一开始就能接受正规治疗的比例,在他所接触的病例中只有三分之二。而错误的医嘱如敷药膏之类,只会起到活血化瘀、让肿瘤更快生长的反作用。
蔡郑东说,正规治疗首先要明确诊断,核磁共振和穿刺活检最有效。确诊后进行2至4次辅助化疗,防止肿瘤转移扩散,为手术创造条件。手术分为截肢和保肢灭活两种。术后则需再做8至12次化疗,防止局部复发。规范治疗周期至少半年,通常情况为9个月左右。
2017年5月16日,蔡郑东给小胖做了截肢手术。

小胖第一次去假肢厂,他知道装了假肢,自己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回学校念书了。文中图片除特殊标注外,均为《人间世》摄制组提供。
手术
思思没有截肢。
她治疗初期的两次化疗效果很好。第二次出院后,却突然“消失”了一个多月。主治医生华莹奇还猜测,她是不是去了北京或者其他医院。
思思在家。临近第三次化疗期时正值“双十一”前夕,上家拼命催货,思思爸妈在苏州开的羊毛衫整烫厂里忙得昏天黑地,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,实在脱不开身带她去上海住院,就打算延后一周再去。思思在如皋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。
奶奶信“大仙”,此前就给思思算过命。“大仙”说治病不管用,思思活不过18岁,还说死后要用破草席裹了从半路丢掉。气得思思妈和奶奶大吵一架,把盘子都砸了。思思爸妈去苏州后,奶奶又去求“大仙”,求来几道符烧成香灰,说喝下去三天就能走路去上学。
“难喝死了。”思思后来皱着眉头回忆。“大仙”还说,这段时间思思不能见爸妈,视频也不行。思思妈忍不住在电话里破口大骂:“菩萨也有妈生的!哪有小孩不能见妈的道理!”但终究是没去见。前后这么一闹就是一个多月,最终是外婆将思思接出来,她才重回医院。
新一轮检查显示,思思肺部阴影扩大,左腿股骨、胫骨、对侧骨盆也都有肿瘤,诊断为骨肿瘤四期(晚期)。肿瘤负荷很重,左下肢肿得厉害,主治医生华莹奇和骨科副主任孙伟建议做截肢手术。
思思妈的眼泪一下就止不住了:截肢?怎么可能呢?她不知该怎么跟女儿说,拉拉杂杂扯了几句,试图轻描淡写地加一句“有截肢的可能性”。正坐在病床上的思思却突然定住了,直愣愣看着她七八秒没说话。然后蓦地眼圈一红,泪珠扑啦啦往下掉,扁扁嘴巴,带着哭腔的声音传出:“我不要截肢!”
那天晚上,思思妈特意打来一盆热水给她洗脚:“我一直摸她的脚趾头,心里就想,万一把脚截掉了,我摸都摸不到了。”
为了不影响孩子,思思妈躲在楼道里哭。小胖妈来安慰,也跟着一起哭。术后化疗对小胖的作用不明显,又很快产生了耐药性,思思入院不久,小胖就开始服用靶向药物“艾坦(阿帕替尼)”。这是被证实在治疗晚期胃癌中,标准化疗失败后,能明显延长生存期的安全药物。
蔡郑东介绍,由于骨肉瘤发病率低,在研究中也不太受重视,科研水平滞后。现有研究中,没有发现与骨肉瘤直接相关的特异性的基因,也就意味着很难进行靶向治疗。靶向药物的使用都是根据循证医学,基于国际经验总结,没有很成熟的方案。
艾坦的副作用明显,其中一项就是气胸。小胖排了5次气,每次小胖妈都要说一箩筐鼓励的话。但背过身去,她自己几度心疼落泪。可日子还要过,还要坚强面对。陪着思思妈哭完,她们又互相打气。
同病房的家属劝思思妈,保命比保腿重要。亲戚们也都倾向于截肢方案。但思思一想到这事儿就哭,闹,撂狠话:“要是给我截肢了,我爬也爬到窗户去跳楼!”
思思妈心里也接受不了,女儿不是天生残疾,养到这么大突然要截肢,舍不得。可如果不救女儿,她觉得自己会后悔一辈子。到了这个关头,对女儿的亏欠感几乎时时折磨着她:多年在外打工,无暇照顾留守在家的女儿,她深怀愧疚。每次见医生讨论病情,站在一边的思思妈总是眼神忐忑地逡巡。
满心的犹豫纠结最后化为一个决心:倾家荡产也要治,但不截肢。
问题回到医生那里,只剩下两种方案:保守治疗就继续化疗,积极争取就想办法做不截肢的手术。孙伟更倾向于保守治疗。一方面已经肺转移,再做一个大手术,遭罪又意义不大,何况不截肢还有复发的可能性。另一方面,思思左腿几乎遍布肿瘤,不像一般人只需换某个关节,这么大面积的手术至少现有文献中没人做过,术后护理也很容易出问题。如果万一又导致并发症,家属不理解,医患矛盾也是麻烦。无论从哪方面看,保守治疗都风险更小。
蔡郑东则主张采取更积极的路线:原发灶在,肿瘤会非常消耗患者的身体,而且耽误一段时间没做化疗,现有药物很容易产生耐药性,只能维持两三个月。做手术减轻肿瘤负荷,切片拿去化验也可以为下一步用药提供依据。“至少还可以做到延长生命,要往这个方向努力,不能眼看着她(很快去世)……”蔡郑东说。
最终,他们决定采取灭活再植的手术方案。简言之,就是将左腿胫骨上的肿瘤全部切除,骨头截断取出,在高温无菌的高渗盐水或酒精中浸泡灭活,再将原骨装回去。
这不是常规的治疗方案,更像是介于医疗原则和人文关怀之间的权宜之计。灭活后股骨功能基本等同于丧失,但满足了思思保存肢体的愿望,相比起更换假体关节花费也更少。“算是给青春期的小姑娘一点心里宽慰吧。而且截肢谁都能做,不一定要到我们这里来做,医生不能嫌麻烦,能多做一点就做一点。”华莹奇说。

手术前夜,思思一家的合影。
思思没意见。肺转移的事她还不知道,以为自己做了手术就能好。手术只要不截肢她就高兴,剩下只有一个要求:做个美容缝合,伤口好看点儿。孙伟听了一乐,保证没问题!
他是主刀医生,相比起美容缝合这点简单的要求,他更担心灭活如何操作——这么长一截股骨,都找不到对应大小的灭活容器。和华莹奇的讨论就像是俩兄弟斗嘴:“用啥灭活呢?”“用盐水啊。”“那用哪个锅啊?”“不管用什么都没那么大的锅啊。要不用消毒盒子?”“消毒盒子全是眼儿啊!”最后终于决定弄个消毒袋,外部靠热水保持温度。

思思的灭活手术持续了6个多小时。
2018年1月11日手术当天,10毫升一支的高渗盐水,医生护士们一起徒手敲了500支。思思从早上七点多被推进手术室,下午四点半才出来。用血费用昂贵,好在还可以互助献血,思思爸爸自己献了,又找了七八个老乡来帮忙一起献血。他和思思妈算过,化疗和手术费加起来要三十万,能省一部分就省一部分吧。
回到病房,掀开被子的瞬间,思思妈捂住嘴,整个人抖得控制不住,伏在窗边失声痛哭。至今回忆起,她仍然一脸心疼:“四块大纱布,一直裹到胸。”
但思思在麻醉清醒后,第一反应是笑了。“腿还在呀。”她说。
死亡,捐赠与复发
手术后思思没怎么戴过帽子,柔软的头皮上一点毛茸茸的青色。化疗初期她曾倔强地保持着室内也不脱帽的习惯,觉得掉发的自己丑。
伤口愈合一段时间后,腿上安装了支具,思思尝试着下床用助步器,妈妈在身后扶着她的腰缓缓挪动。但每一次抬腿她都忍不住皱眉,没几步便大汗淋漓地回到床上,哭起来。
春节前,思思爸爸动手给轮椅安装了一个腿部支架。回到家的思思很少笑,吃药时眉头总是皱成一团。偶尔她会坐在门口的长椅上,晃着右脚,像是在思考,又像是没什么表情。

2018年的春节前夕,羊毛衫厂的工友们一起吃了顿年夜饭,思思也得到了自己的新年礼物。

2018的春节,一家人回到了如皋。思思说她许下了这一年的心愿。
彼时的小胖已经回到南宁家中。骨肿瘤肺转移的感觉就像肺里生出骨头,一点一点地,人就喘不上气来。和思思一样,小胖也不知道自己肺转移。父母骗他说是气胸压住了肺,所以一直要插氧气管,也正好鼓励他做排气。“他会看我的眼色。所以我给他脱衣服的时候都很淡定,还说哎呦看起来好点了嘛。还是那么自然,他就不恐惧。”小胖妈回忆。
艾坦的副作用太明显,服用后期,小胖锁骨下方两侧各开了一个硬币大的洞,吊着两根长长的管子。还有口腔溃疡,皮肤溃烂化脓……有一天晚上,实在太难受的小胖哭得接近崩溃,说自己坚持不下去了,又说想回学校读书。小胖妈哄他说,不要哭那么大声了,会压到肺。他就渐渐止住。
小胖妈心里的无助却像潮水一般久久无法退散。她能感受到儿子强烈的求生欲望。小胖总问她:“医生怎么还治不好我呀?”又说:“如果肺不好,我能不能换肺?”小胖妈说好,如果能换,就把自己的肺给他。后来她真去问了医生,医生说没有太大意义,因为即使换了肺,癌细胞还是会转移过去。
3月15日是小胖的生日。生日前三天,小胖停止了呼吸。
在听说了小胖病情危急的消息后,跟拍了他们将近一年的《人间世》导演谢抒豪也赶到了广西南宁的医院。他回忆到,小胖和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,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说完后,医生沉默了。病房里是死一般的沉寂。氧气瓶内的氧气通过瓶芯与水接触,咕咚咕咚的声音,大得吓人。拼尽最后的力气,小胖紧紧握着妈妈的手,他的手因为化疗已经溃烂了。他望着妈妈,说了最后的一句话,“妈妈,我爱你。”谢抒豪回头看了一眼摄像许伏金,已经哭成了泪人。
小胖妈做出了一个决定:捐献小胖的眼角膜。从小胖开始治疗到过世,她觉得遇到了很多好心人,医生、护士、其他病友和家属,还有朋友,都曾给予她和儿子关心、安慰、陪伴和鼓励。“火化呢也是一堆灰,干脆把眼角膜贡献出来,起码做点功德。我们也回报一下社会。”小胖妈说。
小胖的眼角膜最终使两个人重见光明。
那时思思正准备做最后一次化疗。手术后化疗效果尚可,右边盆骨的肿瘤和肺转移都得到控制。3月20日化疗完当天,爸妈带着她直奔厦门。旅游的4天里,思思笑得比过去半年都要多。

过了年,思思妈还是决定带女儿去次厦门,这是一家人第一次出门坐飞机旅行。
直到肿瘤复发。4月底,思思回到上海。化疗的耐药性渐渐展现,右侧骨盆处的病灶开始疼痛,且因位置特殊,无法通过手术治疗。左腿无法移动,右边臀部疼痛,这一次入院,思思不仅无法走路、站立,甚至连坐着都难以承受,只能全天24小时都躺着。
护士给她早晚各打一次止痛针,但药效过去的时候,思思还是会在床上辗转反侧、捶床呻吟。思思妈有一次几乎是踉跄着跑到护士台前,眼睛像水龙头似的往下掉泪:“还有没有办法啊?她疼得不行啊!”女儿前一晚痛的时候,一度喊着“我活够了,我要死了”,她想着这日复一日似乎永远望不到头的折磨,恨不得抱着思思一起从楼上跳下去。
华莹奇说,常有家属来问如果病治不好,那能不能满足一个小小的要求,就是让病人不要痛,能舒服平和地度过最后的日子。但这“小小的要求”恰恰无法做到——止痛针可以暂时镇痛,但只要肿瘤无法抑制,就会继续痛。
化疗不行,只能考虑放疗和靶向药。放疗周期45天,大约需要六七万元。回老家会便宜点,到如皋市的定点医院能报销大约60%左右;上海的医院没联网,算下来只能报销20%。
纠结了一阵,思思妈最终还是决定不回家,哪怕贵,论治疗她还是更相信这里。
可她迟迟不敢让女儿服用市面上的靶向药。小胖去年吃艾坦时的痛苦,她还历历在目,她不忍心让女儿受那个罪。
病友家属之间还流传着另一种靶向药,思思妈看别的小孩吃过,看起来副作用稍轻一些,但需要托关系从德国或者印度私下购买,价格是艾坦的四倍,平均一个月要一万二。

病房里的孩子们总是在群里讨论病情。
“说白了,最后就是人财两空的事儿。”思思妈说。从女儿得病,一直是她在陪床,思思爸在苏州继续工作赚钱,或者借钱,保障医药费。家里经济压力不小。
思来想去好几天,思思妈最终还是决定,吃贵的那种:“我说过,倾家荡产也要治。”女儿的结局就在眼前,但她没法放手。
“我好想回家”
自放疗开始,思思越发沉默和烦躁。每隔一会儿就哭天喊地说屁股疼,说叫护士来打止痛针又不肯。一会儿说怕上瘾,一会儿又说打了也没用,还是一样疼。由于无法下床,放疗要由护工推着床去另一栋楼做。
腿部放疗还好,提起右臀部也要放疗,她就一脸抗拒,声音带上了哭腔:“屁股不能做放疗呀,做了放疗大小便失禁了怎么办?万一瘫痪呢?”说着便伤心起来:“瘫痪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?……我不要人照顾!我不要做一个废人!”
那时她已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月。无聊的时候,思思常常望着窗外发呆,或者摆弄手机。有时候会莫名哭起来:“我搞不懂……为什么要救我?”有长辈探望,送来一束花,思思捧着拍了照片,很开心,但第二天就一直放在地下,有人说拿花瓶养起来,她不耐烦:“我自己都养不活,我养它干嘛?”
放疗的住院周期漫长,她几次提到“再也不想在医院待着了”;可疼起来的时候,又哭着抱怨妈妈为什么不早点给自己吃靶向药。思思妈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她猜女儿在网上查过止痛针的费用,估计她也心疼钱;也可能偷偷查过自己的病,觉得不妙。
但她不敢想这是否代表着女儿已经知道了什么,不想再继续治疗。也不愿去谈这个话题,怕给女儿增加压力和心理负担。思思爸也说:“善意的谎言嘛。小孩子只能骗,能骗一天是一天。”他和思思妈的想法很统一,就是要让女儿在这个世界上再多待几天。

思思妈觉得给女儿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。
2018年6月初,他去医院送钱,那时候思思的臀部经过一段时间放疗,已经不疼了。但她说自己不能咳嗽,一咳就呼吸疼。“爸爸我们不治了,回家吧。”她说。
思思爸哭了。他觉得女儿可能也有点明白,只不过也在骗自己。
和记者发微信时,思思语气平淡:“我肺里又有肿瘤了。医生说肺部也要做放疗。……天天晚上睡不着。我好想回家。”
(文中“小胖”为昵称,“思思”为化名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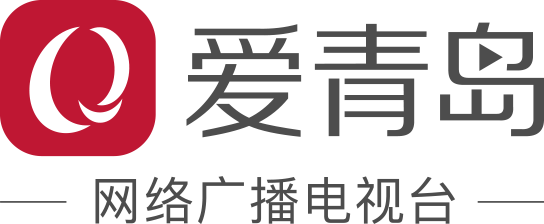

 公安备案号:37020202000242
公安备案号:37020202000242